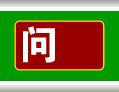| 理易与心易 |
| 无论是推易断卦还是其他任何一种数术预测方法,最令人们感到棘手和头疼的就是如何在林林总总、丰富万千的信息大海中进行取舍,如果用数学来比喻,起卦、排盘等等相当于构造方程式,而分析预测则相当于求解。由于所有的数术都是也只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全息映象或近似模拟,因此这个所谓的预测方程从本质上讲必然是多解的,如何在这众多的解中进行择选、组合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成为卜筮的关键所在,也是对卜筮者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 为了解决预测方程解的不确定性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努力,特别是从宋代以来,发明了许多方法,什么纳甲、纳音、纳星、纳神、式盘等等,但似乎效果并不理想,预测的人劳心费神地忙乎半天,最后面对成式依然是一头雾水,即使能得出一点结论,准确性也差强人意。 我在学易过程中,发现了几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1、早期特别是三代、春秋以上的占卜,准确性普遍较高,而后世特别是宋代以降的预测,虽然所用方法丰富复杂了许多,但准确性总的讲不如上古、中古; 2、上古预测所用方法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无非就是起卦、断卦两个环节,似乎并没有用什么复杂高深的式盘等等, 而准确性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3、从古至今,真正有据可考的易学大家,其预测实例所用的方法也都很简单,而后世那些所谓懂得奇门、太乙、六壬等高深数术的所谓高人,在正史中并不入流。也就是说,这些所谓掌握了高深数术的高人,恐怕传说多于实际。典型的如诸葛亮,本来只是一个杰出的谋略家,却被后人带上了许多虚构的光环。 上面这些事情令我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自宋代以降(也许更早到汉代)所做的所谓对数术的精确化、定量化努力,是否走入了歧途? 仔细考察分析这些复杂化、精确化、定量化的工作,不难发现他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是企图给《易》注入更多的逻辑内涵,即试图发现或发明一些具有确定性的逻辑规律,再通过这种逻辑规律进行推演预测。用哲学术语讲,这种思路也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和运用,我们把这种治易方式称为“理易”,即“以理解易”“穷理断易”,这种方法正如同西方科学传统那样,以解析(而不是综合)、细分(而不是统摄)、定量(而不是定性)、形式逻辑(而不是辨证逻辑)等为特点。我想,全部问题和毛病就出在这里! 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你因为长期的修炼或偶然的顿悟而逼近宇宙和人生最隐秘的境界时,都会有一种似有似无、若即若离、捉摸不定的恍惚之感,你似乎明白了许多但似乎又难以讲的明白。恍兮惚兮,隐然有象。《易经》作为对宇宙和人生精微玄妙的映象和模拟,其本身也正具有这种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性质。因此,易经的模糊性实在是她所要反映的事物(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模糊性决不等于空无,正是在这种看似模糊的混沌之中,蕴涵着宇宙、人生、社会的全部信息。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事物所内涵的有用信息量跟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明晰性是成反比的,越是清晰确切的事物,所涵的有用信息就越少。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确定性的获得,往往是以对信息完备性(全息性)的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看来,《易经》的模糊性正是它的全息性的必须。 道,可道,非常道。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当进入到宇宙的最隐秘处时,实在太幼稚和苍白了。正象许多常规的物理定律在黑洞那里或量子世界会失效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驾轻就熟、清清楚楚的那些形式逻辑规律、那些语言等等,当面对宇宙的至精至微时,似乎全都失去了作用。因此,所有那些企图用清晰的逻辑、用如同1+1=2这样明确的推理来解释和判断易经的努力,正如企图骑着自行车上月球一样,从根本上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就陷入了不可知论呢?不是。佛性人人都有,只不过受到了蒙蔽。对宇宙最隐秘处的关照和体认,只能靠心。凝神净心,感而遂通。以此来解易、断易,谓之“心易”,其法至简而其应至神。实际上,如果一个人的心性修为到了一定的层次,根本不需要卜筮就可以预测,佛门称之为“神通”,道家美其曰“妙算”,儒家赞之为“善易”。妙算者不算,善易者不卜,此之谓乎。 当然,要达到这种上乘的境界,需要长期的修炼和仰观俯察的经验积累,对于一般的卜筮者怎么办呢,这时候易象、易数、易理就该发挥作用了。象、数、理并不会给出我们完全具体的答案,它们的唯一作用是诱发、启迪和导引我们的灵力,具体的答案,取决于物与我、心与境的混融和刹那间的灵光闪现。 因此,我不太主张过于看重卦辞、爻辞,更不主张进行烦琐的推演和牵强附会的组合分析,这些东西往往更加蒙蔽了我们的心性,固结了我们的灵力。对还在苦苦钻研那些所谓高级预测术的同修们,我想奉劝一句:与其劳神费力、事倍功半地沉陷于那些烦琐庞杂的枝蔓之中,不如放下,转而向内,修明自己的心性,酝酿自己的悟性,磨砺自己的灵性。你会发现,打开宇宙神秘之门的钥匙,原来就在眼前,用不着骑驴找驴。 绝圣弃智,此其谓乎! |
7378844412 2025-07-24 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