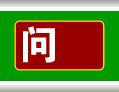在我们北京,哈德门——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外,有条花市大街。过去,那可是个繁华的地方。街道两边净是些大买卖,街边上小摊小贩也很多,可最多要算看相测字的啦!
明末清初,那儿有个测字先生姓邵,叫邵康节[邵康节(1011-1077),北宋哲学家。名雍,字尧夫,谥号康节。范阳人。后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屡授官不赴,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为百源先生。邵康节研究阴阳八卦,参杂道教思想。过去看相测字等迷信职业者,都把邵看作祖师爷。这段相声以邵为明末清初时人,并出现在北京,虽然是附会之说。]大家都说他测的字灵呀!因此他的生意就特别好,别的卦摊一天难得看仁俩的,有的还能两三天不开张。为什么呢?满嘴的江湖话,净骗人,可不康节先生就不一样啦!出口成章,按字义断事。首先大伙听着次不讨厌。至于是个是个个部灵,那可不能那么说。因为他名声大,即便算得不准,大伙儿也都说“差不离”。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儿个人崇拜。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声呢?因为他给皇上测过字。大伙儿想:皇上都找他测字,那还能没本事吗?所以上他那儿测字的犹多,生意就比别的那些卦摊都好。
他给哪个皇上测过字呀?明朝的末代皇帝明思宗——崇侦。啥!这也是个倒霉的皇上。过去有句俗话“倒霉上卦摊”嘛!要不是倒霉,能去测字吗?
崇侦不是住在官里头嘛,他怎么跑到花市大街去了呢:因为闯王李自成、大西王张献忠还有十三家造反啦!闯王的起义军已经快要打到北京城啦!城里可透着有点儿乱。他微服私访,打算悄悄打听打听老百姓对朝廷有什么议论。再说天大打败仗,他在宫里也烦呀!
他一个人,连贴身太监都没带,脱下龙袍换上一身老百姓的衣裳,带了点儿散碎银子,就出了皇城啦,溜溜达达地就来到花市大街啦。见甬路边上围着好多人,崇祯踮起脚跟住里一看,原来是个测字摊。只见一人刚测完了字,对测字先生说:“邵先生,您多受累
了!我回去照您的话去找,准保能找到。”说完这话,付了卦金,转身就走啦。看热闹的也散啦。崇祯心想:原来这位就是邵康节,怪不得这么多人围着看哪!——连住在深宫的皇上都知道邵康节的名字,您想,他的名声有多大?人一散,邵康节的卦摊就亮出来啦。
崇祯一看这个邵康节长得倒像个念书的人儿,六十来岁,花白的胡须。身上穿得也挺干净。面前摆了个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块小石板,半截石笔;一个木头匣子,里面放着很多的字卷儿。要是测字呀,就抓个字卷儿。不抓字卷儿,在石板上写个字也行。不会写字的呀,嘴说个字儿也可以。
崇祯一想:我这皇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啦,不如测个字问问,我这江山还保得住保不住呀?
“先生,请您也给我测个字儿。”
“您拿个字卷儿吧。”
崇祯心想:他那字卷儿不能拿。写那些字卷儿都是他自己选的,哪个字他都编得有词。“我甭抓啦!”
“那您写个字也行。”
崇祯又想:我也别写了。“干脆我说个字吧!”
“那也好。”
“我说什么呢?”崇祯想。正这么个时候,从背后过来两个过路的,一边走一边说:“兄弟!你开玩笑怎么没完没了的,还有没有完啦?”
崇祯一听:有完没有?嗯,我就测个“有”字吧。“先生!我说个‘有’字吧!”
“哪个有呀?”
“就是有无的有。”
“噢!”邵康节拿起石笔,在小石板上写了个“有”字。“您问什么事呀?”
“我是为国担忧呀!我打算问问大明江山还保得住保不住呀?”
邵康节一听,心里打了个顿:面前站着这位是谁呀?一不问婚丧嫁娶,二不问丢财失物,单单问这大明江山保得住保不住呀?一定不是平民百姓。他回头看了看,卦摊周围有没有看热闹的人。他干吗看呀?他看看要是有人他就不敢说啦。怎么啦?因为那年头是“莫谈国事”呀!万一看热闹的人里头掺杂着一两个东西厂锦衣卫的人听去了,那邵康节就麻烦啦!什么是东西厂、锦衣卫呀?就是专门替皇上打听消息的,谁说了对朝廷不满意的话,当场就能给抓走。
邵康节一看,幸好,卦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小声跟崇祯说:“老乡!这个字您问别的什么事都好。”
“怎么呢?”
“‘有’嘛,没米有米,没钱有钱。您问大明江山保得住保不住呀,可不老太好的。”
“你不是说‘有’嘛,没什么都有哇,怎么问到江山这儿就不好了呢?”
“您问的是大明江山呀!这个‘有’字就不能那么解释啦!您看这个‘有’字,上头一横一撇是‘大’字的一半;下头‘月’字是‘明’字的一半。大明江山上下都剩下一半啦,您想那还好得了嘛!”
崇祯一听,心里吓了一跳:解释得有道理呀!可脸上不能带出来。“先生,我刚才说的不是有无的‘有’,是朋友的‘友’。”
邵康节在石板上又写了个“友”字。“这个字您问什么事呀?”
“还是问大明江山呀!”
邵康节说:“您这个‘友’字还不如刚才那个‘有’字哪!”
“怎么回事?”
“您这个字形是‘反’字出头哇,‘反’字出头就念‘友’呀。反叛都出头啦,大明江山可就危险啦!”
崇祯心里又咯噔了一下。马上改口说:“先生!刚才那两个‘有(友)’字我都说错啦,我是要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个‘西’。”
“噢!您说的是申酉戌亥那个‘酉’呀?”
“对啦!”
“还是问大明江山吗?”
“哎!”
“那可就更糟啦!”
“怎么更糟啦?”
“啊!这个‘酉’字还不如刚才那两个哪!不但大明江山保不住,连皇上都得不到善终。”
崇祯一听,脸都白啦!“怎么皇上还不得善终呀?”
“您想嘛:天下数皇上为‘尊’呀!皇上是至尊天子呀!这个“酉’字就是‘尊’字中间那箍节儿(北京土话,一段的意思)。您说这个‘尊’上边没头,下边没腿,这皇上还活得了嘛!连皇上都缺腿少脑袋,这大明江山还保得住吗!”
崇祯一听:这话有理呀!这江山是保不住啦。我连脑袋跟腿都没啦,还活什么劲儿呀?为了保住全尸,连皇宫都没回就上煤山啦——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找一棵歪脖树就吊死啦!
历史上说,崇祯是在李国祯棋盘街坠马后(崇祯手下名将,被闯王在棋盘街刺伤坠马身亡),闯王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才上煤山上的吊嘛——那是史书误
记。那阵崇祯已吊死半个月啦!王承恩才去凑个热闹,想在历史上留个忠君尽义的好名声——沽名钓誉嘛!他找皇上找了十四五天都没找到,后来才在煤山看见崇祯在那棵歪脖树上吊死啦,怕回去不好交差,心想:干脆我也在这儿将就吧!太监王承恩这才在崇祯脚底下吊死的。他们俩上吊前后相差半个月哪!历史上说两人一块儿死的,那是小道儿。我这才是正根儿哪!
闯王迸了北京啦,市面上也平静啦,邵康节上景山遛弯儿去啦。一看,歪脖树上挂着一个。“我认识呀!噢!不就是那天找我测仨(有、友、酉)字的那位嘛!再一看,下边吊着个太监。“噢!这甭问啦,肯定是崇祯皇上呀!哈哈,我说皇上不得善终,怎么样?上吊了吧?我字儿测得灵呀!”从这儿邵康节逢人便说,见人就讲,他给崇祯皇上测过字,灵极啦!这一宣传呀,就有那么些人爱传话,一传十,十传百,邵康节更出名啦!
这话传来传去就传到九门提督耳朵里去啦!这个九门提督是满人呀!闯王手下哪来满人呀?因为李自成进了北京城,骄傲啦!腐化啦!铜棍打死吴兵部,占了陈圆圆,把在山海关的吴三桂可给气坏啦!“冲冠一怒为红颜”嘛!吴三桂这才下沈阳搬清兵,当了汉奸啦!九王爷多尔衮带兵进关,李自成战死湖北九官山啦。江山易鼎,改国号为清啦。我刚才说的那位九门提督换了满人啦。
当时的九门提督权力可不小,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呀!内九门就是:前、哈、齐、东、安、德、西、平、顺,九门提督衙门就设在哈德门里头。内城那八座城门都挂的云牌——“点”,唯独哈德门挂的是钟。九门八点一口钟嘛!因为九门提督衙门设在哈德门那儿哪!他那儿一敲钟,其他的八个城门跟着敲点:“关城喽!”——您说他权力大不大?
这个九门提督不但是满人,还是正黄旗,黄带子,铁帽子王爷呀!街面上传说邵康节字测得灵呀!给崇祯测过字,说皇上不得善终,崇祯真上吊啦!这话可就传到九门提督耳朵里头去啦。怎么那么快呀?九门提督衙门就在哈德门里头,邵康节就在哈德门外头花市大街摆卦摊儿,没多远呀!那传得还不快嘛!
九门提督听到这话儿,说是妖言惑众:世间有这事儿,测个字就能知道生死呀!这都玄啦!我就不信有这样的事。找他去,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事!提督大人换上便服,出了辕门,跨上骏马,后边跟了八个亲兵小队子,保护大人。就出了哈德门啦。到了花市大街,大人一看,嚯,卦摊儿还真不少,哪个卦摊儿是邵康节的呢?问问。当时翻身下马,这会儿来了个过道儿的,九门提督怎么问呀?他一挽袖子,眼睛一瞪,冲着这个过道儿的,“站住!”
把这位吓了一跳。“干吗呀这是?凶神附体啦!……”
“我问问你,邵康节在哪儿算卦?”
这位一想:有你这么问道儿的吗?我该告诉你呀!刚想发作。仔细这么一瞧呀,又吓回去啦!怎么?他看见这位屁股后头还跟着八个弁兵哪!其中一位拉着马。他不敢发作啦,这位小不了,他说:“您问邵康节的卦摊呀,这儿不是嘛!”
说着他手往马路下一指。怎么往下指呀?在明、清那会儿,马路叫甬道,路面比便道高。提督大人顺着他手往便道一瞧,果不然有个卦摊儿。他就奔这卦摊儿来啦!
“你叫邵康节吗?”
“啊!”刚才他问道儿的时候,邵康节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心想:甭问,这位来头不小呀!
“我听人说你测字灵呀?”
“那也不敢这么说,反正八九不离十呀!”
大人一听,嚯!口气不小呀!“你给崇祯测过字呀?”
“啊!”
“你说他不得善终?”
“他煤山上吊啦!”
“那我问问你:我能不能善终?……嗐!我问这干吗呀!你也给我测个字。算对喽我拿一两银子给你。算不准我可砸你的卦摊儿。”
艺高人胆大,邵康节并没心虚:“您拿个字卷儿吧!要不说个字,写个字也行。”
“那我就拿个字吧!”大人一伸手,就在小木匣里拿了个字卷儿。邵康节接过去一看,是个“人”字。
“此字念‘人’。您问什么事呀?”
大人一想:我问什么事呀?我没事儿。我赌气来啦?心里这么想呀,嘴里可没这么说。“我呀?……我是让你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
邵康节一听,心想:有你这么测字的吗?你是什么人,你自己还不知道嘛!你还用得着测字吗?噢,这是考我呀,找我赌气呀!
邵康节抬头把九门提督上下打量了几眼。看这位六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穿得好:宝蓝横罗的大褂,琵琶襟的坎肩;头上戴了顶纱帽头儿,正中一块帽正是碧玺的;一伸手,大拇指儿戴了一个翡翠的扳指儿,水头儿好,是真正的祖母绿呀!再说他说话那派头儿,显着他财大气粗。嗯!甭问,八成是个当官的。“您要问您是什么人呀?您是一位当官的老爷。是位大人。”
“嗯!”他心想: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呢,认识我呀?不能呀!也许是从我的衣着打扮看出来的。既然他看出我是当官的啦,我再问问他我是文官武官?这他就看不出啦。
‘不错!我是个当官的。你再给我算算,我是文官还是武官?”
邵康节一听:这,我怎么知道你是文官武官呀?有这么测字的吗!可是,再仔细一想呀,大人是骑马来的。武官骑马,文官坐轿嘛!大拇手指儿上还戴了个扳指儿,那是拉弓射箭用的东西,噢!八成是武职官:“大人!您要问您是文职官武职官呀?”
“啊!”
“您是武职官。”
大人一听:哎呀!他还真有两下子哪。“对!我是武职官。你再给我算算我是几品官?什么官衔?”
“这?”邵康节心想:这我没法算。武职官多啦:提、镇、副、参、游、都、守、千、把、外委。我知道你是什么职位呀?又一想:算不准都要砸我卦摊儿,要不算还不得给我发(古时刑罚的一种。即充军发配。)了啊!“您是什么官衔呀?……”邵康节说话怎么拉长声呀?他想词儿哪!他一想:这位是穿便服来的呀,要是穿官服来的就好啦!那还用说吗!官服上前后有补子:文禽武兽。大帽上有顶子:红、蓝、白、金。他一看就知道啦!这位穿的是便服,看不出来呀!“您……您……是几品呀?”邵康节一眼看见大人身背后那八个亲兵小队子啦!大人穿的是便服,可他们穿的都是号衣呀!头上打着包头。号褂子外边套着大红坎肩,青布镶边儿。前后心白月亮光儿。有字:后背心是个“勇”字,前心是“南司”。邵康节笑啦!知道啦!南司是提督衙门呀,北司是顺天府——好嘛!大人身上虽然看不出来呀,可他小队子给他戴着记号哪!“回大人的话,您是当朝一品呀!”
“什么官衔?”
“您是九门提督兼五城兵马司——军门大人。”
“啊,神仙呀!我就不信你测字这么灵,三天之内我非砸你的外摊儿不可。”一赌气就要走。
邵康节说:“启禀大人,您还没给卦金哪!”
“啊!差点把我气死,你还要钱哪?”
“军中无戏言嘛!”
九门提督往他摊儿上丢了块银子,约摸有一两多重。带着人就回衙门啦!——合着闹了一肚子气,还花了一两多银子。“花钱买生气”就是那年头儿留下的。
大人回到提督衙门连饭都没吃。晚上气得睡不着觉。干吗呀?他想主意哪!打算想个主意把邵康节的卦摊儿给砸了!“我说三天之内砸他的卦摊儿,我非砸不可。军中无戏言嘛!”
要说在那种社会,甭说身为九门提督,就是一个弁兵,砸个卦摊儿还不容易嘛!就是剐了测字的也没什么了不起,随便加个罪名就办了。可是堂堂九门提督为了表示自己有能耐,不想随便砸摊儿抓人。他还真想试试邵康节,如果真会神机妙算,还想保荐他当军师哪!
大人一宿没合眼,想了一宿想出个主意来。这个主意可损点儿。天一亮就起来啦,要搁着往天还睡哪。今天他憋着砸邵康节的卦摊儿哪!到了书房把伺候他的给喊起来啦,这跟班儿的叫来喜,四十来岁,细高挑儿,有点水蛇腰,外带是个八字脚。这个样子是好的呀!大人往哪儿一坐,他往旁边一站,甭弯腰,那毕恭毕敬的样子就出来啦!
“来喜呀?”
“哎,伺候大人。”
“今儿你也别在家里伺候我啦,你把我的官服换上,带着八个亲兵小队子,上花市大街找邵康节那儿测个字。什么事你都甭问,就问他你是什么人?他只要说你是当官的,回来跟我说,我就赏你五两银子,带人去砸他卦摊儿。”
“哎,是大人。”
老妈子从后面把大人的官服拿出来啦,来喜把官服一换就往外走。
“回来。”
“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到那儿千万别拿他那写的字卷儿呀,那有毛病,你自己写个字吧。”
“回大人的话,小人没念过书呀,不会写字呀!”
“浑蛋!连简单的都不会写吗?你就写个人字儿就行啦,一撇一捺,这还不会嘛!”
“是,是!”
班儿的来喜出了辕门。大人早吩咐下来啦,八个亲兵小队子拉着马在那儿等着哪。来喜骗腿上马,小队后边跟着,来喜心里这个美呀:想不到我这半辈子还当了这么会儿九门提督。到了花市大街甭找啦,小队子昨天来过呀,认识。拉着马就到了卦摊啦,来喜翻身下马。邵康节一看:怎么?九门提督又来啦,砸我卦摊儿来啦。再仔细一看呀:怎么今儿这位九门提督不是昨天那位啦?北京城有几个九门提督呀?不就一个嘛!睡了一宿长个儿啦。又一看:没错!是九门提督,后头那八个亲兵小队子还是昨儿那八个呀!再一看来人身穿袍褂;前后麒麟补子;头上戴着凉帽枣红顶子——从一品,双眼花翎,冲这套官服准是九门提督呀!——多新鲜呀,这套衣服本来就是他的嘛。可是他再仔细一瞧这人呀,砸啦!体不称衣呀,人瘦衣裳肥。穿在身上就像竹竿挑着这套衣服似的:耸肩膀,水蛇腰。脑袋不大,眼睛倒还机灵,望着邵康节滴溜溜转。下巴颏有几根虾米胡子,凉帽往他脑袋一扣,差不多底下就没什么啦!邵康节一下就看出个七八成啦——冒牌儿货!
“邵康节给我测个字。”
邵康节一听:怎么着?认识我呀!“您是写字呀,还是拿字卷儿呢?”
“我自己写吧!”
邵康节把石板石笔递给他啦!来喜拿笔就像拿旱烟袋一样,五个手指头一把抓。好不容易才画了个“人”字,把汗都憋出来啦!您想,他又没念过书,那字写出来能好看嘛?一撇一捺拉得老长,两笔挨得挺紧。这个“人”字就跟他那长像差不多:细高挑儿。“字随人变”嘛!
邵康节把石板接过来一看:“此字念人。您问什么事呀?”
“我没别的事,你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
邵康节一听:今儿这个怎么跟昨儿那个问的一样呀!甭说一定是昨儿那个九门提督派来考我的。我说得不对他好砸我卦摊子呀!他派衙门里谁来啦?是幕府师爷呢还是听差的呀?嗯,不是师爷,师爷能写这样的字吗?再仔细一看,这人往卦摊前一站,手就耷拉下来啦,水蛇腰儿,耸肩膀,俩眼睛净往地下看(比划)。站在老爷身边伺候惯了,那样子就出来啦。对,不是师爷,是跟班儿的。
“要问您是什么人呀?”
“啊!我是什么人呀?”
“说出来您别生气。您是别人坐着你站着,别人吃饭你看着。
你是个站人。甭转文说白话儿,你是个跟班儿的,伺候人的!”
“啊!他真算出来啦!”——哪儿是算出来啦,是看出来啦。
来喜赶紧就走。邵康节说:“你还没给卦礼哪!”
来喜正想发脾气,可是见街上人多,怕丢“大人”的面子,只好乖乖地在身上摸了几个制钱,往桌上一丢,就回衙门啦。
邵康节一看,笑啦:“没错!就冲他给这卦礼就是个跟班儿的——舍不得花钱嘛!”
来喜回到衙门,到了上房。“跟老爷回话,我回来啦。”
“邵康节跟你说你是什么人呀?”
“他说小的是别人坐着我站着,别人吃饭我看着,是个站人。甭转文说白话,我是个跟班儿的。”
老爷一听,把鼻子都气歪啦!“浑蛋,他愣会算出来啦!你叫什么来喜,干脆明儿你改名叫报丧吧!”——这个九门提督算计不过邵康节,对底下人出气啦。
大人越想越气,一转脸见太太进来啦!“太太,您辛苦一趟,上花市找邵康节去测个字,写个人字儿就行啦!别的也甭问,就让他算算你是什么人?”
“哟!老爷我行吗?”
“行,行!太太出马,一个顶俩嘛!”——这叫什么词儿呀?“他要算错了我带人去砸他的摊子。”——他憋准喽要砸邵康节的卦摊啦。
太太说:“既然老爷这么吩咐,我就去一趟吧!”
“别忙!你穿这身儿去不行,那他还看不出来嘛!换换,换换。把老妈子那身儿换上。把首饰,什么镯子、戒指、耳环子都给摘下来。头发也梳梳,梳个苏州髻。”又吩咐丫头:“去,上厨房弄点锅烟子来,给太太脸上抹抹,让他看不出来。”——您说这位太太是招谁惹谁啦,图什么许的呢?“你还别坐轿,坐骡车去。到了哈德门就下车,别让他看见。你记清楚喽!出城门左手第三个卦摊就是。”——好嘛,这位老爷可真用心呀!
这位太太还真听话呀!打扮好喽坐着骡车就奔哈德门来啦。在城门洞就下了车啦,数到第三个卦摊儿一看,没人测字。
“哟!您是邵康节老先生吗?”
“是是。您测字吗?”
“对啦!”
“您拿个字卷儿吧?”
“不价。我写个字吧!”
邵康节把小青石板、石笔递给太太。她就在石板上写了个“人”字。写完了把石板往桌上一放。顺手把半截石笔就搁在石板上啦。说来也凑巧,她那石笔正好搁在“人”字的上半截啦!这样猛一瞧“人”字头上加一横,就成了个“大”字啦!邵康节问:“您问什么事呀?”
“没别的事,您给我算算我是个什么人?”邵康节一听:这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呀,怎么都问是什么人呀?我看呀你们都不是人,吃饱了没事跟我测字的捣什么乱呀!邵康节一看这“人”字头上搁着石笔,嗯,人字头上加一横不是念大字嘛!再仔细一看。嘿!真有这么凑巧的事,刚才来喜写的那个“人”字没擦干净,留下了一点儿。这一点儿不歪不斜正留在“大”字的下边,三下喽这么一凑合呀,这个“人”字就念“太”字啦!“八成是位太太呀!这?不像呀,这份儿穿章打扮,一脸的滋泥,有太太不洗脸的吗?又仔细一想:刚才她写的时候手伸出来可白白净净,胖胖嘟嘟的跟白莲藕似的。要说这个人怎么长的呢?这不是姜子牙的坐骑四不象嘛!嗯,刚才我看她那手腕子上跟手指头上还有印子,那是戴首饰留下的呀!甭问刚摘下去。要是老妈子能戴得起吗?莫不是九门提督故意叫他的太太取掉首饰,打扮成这样考我来啦?要砸我的卦摊儿呀!嗯,错不了。一定是九门提督的太太。
“您要问您是什么人呀?……”
“我是什么人呀?”
“您是位太太。”
哟,我这扮相都唬不住他呀!赶紧给了卦礼回衙门啦。到了上房,还没容老爷问哪,她就说啦:“老爷!邵康节字可测得真灵呀!他说我是太太。”这句话刚说完,气得老爷汗都下来啦——你说这是何苦呢!
老爷一看张妈站在太太旁边哪!“张妈!你赶紧换上太太的衣服,把太太的首饰都戴上。带着另外四个老妈伺候着你,就坐着太太平时坐的那乘八人绿呢大轿,上花市大街找邵康节测字去。就写个人字儿就行啦!人字儿会写吗?这么一撇,这么一捺,瞧清楚了没有?问他你是什么人?他绝算不出来你是老妈子。他看你这打扮,一定说你是太太,还是大官的太太。他只要说你是太太你就回来跟我说,我重重有赏。赏你五两银子,我带着人去砸他卦摊儿。”——他是非砸邵康节的卦摊儿不死心呀!
张妈照着老爷的吩咐把太太衣裳换上啦!戴上首饰。老爷一看:“不行不行!把头梳一下,梳成两把头,脸上再擦上点胭脂粉,头上也得戴首饰,插点花。鞋不行呀!换上花盆底儿。”——老爷用心呀!从头到脚下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检查,亲自指挥。一点破绽都没有啦,才说:“去吧!带点儿零钱给卦礼。”——想得周到呀!
张妈出来,坐上太太的八人绿呢大轿。后边跟着一辆骡车,坐着四个老妈子就上花市来啦!到了邵康节卦摊儿那儿,轿子打杵。四个老妈子赶紧掀轿帘儿把张妈搀下来——嘿,老妈儿搀老妈儿呀!
邵康节一看:来了位太太。还没说话哪,张妈就先开腔啦:(三河县口音)“先生!您老给我测个字吧!我不拿字卷儿,我自个儿写。”
邵康节一听:哟!太太说话怎么这味儿呀?三河县的县知事的夫人来啦!赶紧把石板递过去啦,不是太太刚走一会儿嘛,她刚才写的那个“人”字还没擦哪!按说张妈把太太刚才写的那个擦了再写多好哇!她没擦,她想:这块石板别说再写一个“人”字,就是再写十个也有地方呀!她拿起石笔就写了个“人”字,正好写在太太那个“人”字旁边啦!
邵康节接过石板一看,是个“人”字。“此字念人,您八成是要问您是什么人吧?”
“对啦,先生您太灵啦!俺还没有说话哪您就知道俺要问啥啦!”
邵康节心想:这还用问嘛,这两天来了好几个写“人”字的啦!凡是写“人”字的都问自己是什么人呀,这不明摆着是串通了来 的嘛,成心要砸我的卦摊儿呀!“您要问您是什么人呀?……”
“哎!”
邵康节一想:看她这阵势,穿章打扮,一定是位官太太。还小不了。坐的是绿呢大轿嘛!一二品大员的夫人呀!八成又是提督衙门来的,九门提督的夫人呀!不对!九门提督能要她当夫人吗?什么模样儿呀!不擦胭脂粉还好看点,这一擦上就跟牛屎堆上下层霜似的。您看这满脸褶子,就跟老榆树皮差不离啦!虽然手上戴满了金首饰,可她这手跟刚才那位的手就不一样啦!那位的手跟白莲藕似的。她这手跟黄瓜似的,一手的口子。甭问,粗活儿做多啦!再说也是巧劲儿,她写的“人”字正好写在刚才那位太太那人字儿的旁边啦!她不是太太,是太太身边的人。哪些人是太太身边的人呀?小姐。有这样的小姐吗?不是小姐。丫头?岁数不对啦,四十好几啦。决不能是丫头。嗯,老妈子?对啦!她一定是老妈子。怪不得她说话是三河县的口音呢?三河县出老妈儿嘛!“你是个老妈子呀!”——他又研究出来啦。
张妈一听:得!我那五两银子没啦!给了卦礼转头就走。
四个老妈过来啦!刚要搀张妈上轿,张妈说:“还搀个啥劲呀,人家都算出来啦!坐啥轿呀,咱们自个儿走回去吧。”她这一说呀,连邵康节都给逗笑啦!
张妈回到衙门,跟老爷一回禀呀,把九门提督给气得直咬牙!“邵康节,我不砸你卦摊儿,我这九门提督不当啦!”——干脆说,不砸卦摊儿,死不瞑目啊!
“来人呀!”
“喳!”
“去到监狱提个犯人来。要提判死刑的,判徒刑的不要。”干吗要判死刑的呀?他跟邵康节拼上啦!难邵康节呀!邵康节万万也想不到死刑犯人还可以上街测字呀!
差人在监狱里提了个死刑犯人。九门提督提犯人狱官还敢不给嘛!是个秋决犯。
在前清死刑有两种:一种是斩立决,就是宣判后就给宰啦!另一种叫秋决,就是秋后处决。每年秋分刑部把当年要杀的犯人名单造皇表,皇上还要上天坛祭天,焚了表后集中一块儿杀!前一种是“零卖”,后一种是“批发”;买主都是阎王爷啊。
带来的这个死刑犯叫“该死”,是个江洋大盗。差人把该死带到后院,往那儿一放。
老爷说:“你判的什么刑呀?”
“回大人,小的判的秋决。”
“你想不想活呀?”
“大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还转文哪。
“唔,我给你条活路。给你打扮打扮,你上邵康节那儿去测字,让他算算你是什么人?他要算不出你是死刑犯,回来就放了你。万一他要算对了,那也是你命该如此。”
该死一听:管他呢!碰碰运气吧!“我谢谢大人。”
“来人呀!”
“喳!”
“把他的脚镣手铐给下喽!找剃头的给他刮脸打辫子。洗干净啦给他换身儿干净衣裳,让他上邵康节那儿去测字。我就不信邵康节能算得出来他是死刑犯!判了死刑还能上街测字吗?”——他这招儿可厉害呀!时候不大就把这死刑犯给打扮好啦。
“来呀。派四个人跟着他。”干吗要派四个人跟着呀?一来怕他开溜,二来万一邵康节要算出来他是死刑犯,拉回来不是还得宰嘛!“你们四个离他稍远点,别让邵康节看出来。别穿号衣啦,都换上便服;带着点儿家伙。听见了没有?”
“是!老爷。”
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怕邵康节算出来呀!
四个小队子押着该死上花市来啦!到了邵康节那儿,该死说:“先生!您这字儿测的灵不灵呀?”
“我这儿测字断事如神。”
“啊,灵呀!”
“灵极啦!”
“哎呀!这不要命嘛!”
邵康节一听:怎么?我算得灵怎么会要他的命呀?这个人语无伦次呀。“您是拿字卷儿呀还是写字呀?”
“我说吧!”
“您说个字也行。”
该死一想:我说什么字儿呀?说什么字也不保险,这可是性命交关呀!干脆我就问他我是什么人?只要他一出口错喽,我撒腿就跑。我这官司就算完啦!“先生,字儿我也甭说啦,干脆您就算算我是什么人吧?”
邵康节一听:噢!他也是算这事儿。八成他们是一事吧!这又是提督衙门派来考我,要砸我的卦摊儿呀!“你要问你是什么人呀?……”
“对呀!”
邵康节又一想:我是什么人?人从口出,也就是口字里边加个人字。这字念囚。噢,囚犯呀!有门儿!连囚犯都给我派来啦,你损不损呀!这?不能呀!囚犯能随便上街测字吗?哎,这是九门提督让他来的呀!九门提督支使囚犯,他正管呀。邵康节又上下打量该死,看他一脸的横肉,走路罗圈腿:这是趟镣趟的呀!罪小不了,都趟上镣啦嘛!又一眼见那四个小队子啦。虽然都换了便服,可长相早认识啦。这两天来了三回了嘛!
“你是什么人呀?……”
“是呀!您快说呀!”
“你是个犯人。”
“啊!算出来啦,完啦!我这脑袋要搬家。你缺了德啦!你呀……”
“你不但是个犯人,你这罪还不轻。你呀,活不了!非宰了你不可。”
该死一听:“我可不是活不了嘛,你算灵啦我还活得了哇!”
其实邵康节也没看出他是死刑犯——他怎么看得出来他判的什么刑呀!邵康节说:你活不了,非宰了你不可,是句气话。心里说:你个犯人跟着咋乎什么呀,起哄呀!我还不骂你两句嘛——邵康节那两句本来是骂该死哪,该死认为邵康节算准了自己是死刑犯哪,要不怎么叫该死呢!
四个亲兵过来啦!锁链往该死脖子上一套。“走!押回去。”
邵康节一看:“怎么样?是个囚犯吧!你们那几手儿还瞒得过我吗?”
小队子回去跟九门提督一回禀。把他给气得呀:“来人呀!”
“喳!”
“把该死给我宰喽,甭等秋后啦!”——得!等不得“批发”就给“零卖”啦!
大人还想主意呀,他不认输呀!天儿都黑啦,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吧。气得他一宿没合眼。虽然他一夜没睡可想起个绝招儿来。什么绝招呀?他往日在院子里乘凉呀,看到房檐下有个燕子窝。他打算就在燕子身上出点主意。第二天一早他叫人搬梯子上房给他掏燕子。当差的一听:我们这老爷是什么毛病呀?要玩儿燕子呀!大人吩咐下来啦,不敢不听呀,赶紧搬梯子上房掏燕子。您想人一上梯子那燕子还不飞嘛,大燕子全飞啦!可小燕子飞不动呀,才长毛儿呀,当差的掏了个小燕子下来啦。大人往手里一摸,叫了二十几个亲兵小队子:“你们每人带根檀木棍儿,走!上花市。”他要砸邵康节的卦摊儿啦!他想:就算你邵康节是神仙,这回你也算不出来啦。
他带着人到了花市,邵康节一看:九门提督又来啦!后边还跟着二十几口子,每人手里提拎着根檀木棍儿,甭问是要砸我卦摊儿呀!我得留神点儿。
“邵康节,我又来啦!我甭说干什么你也知道。前天我说:不出三天你只要有一回没算准,我就砸你卦摊儿。咱们说的是三天为限,今儿是第三天啦!这就叫‘军中无戏言’。昨天那些什么太太、老妈子、死囚犯都是我派来的,就是要……我都告诉他啦!——告诉你啦你也得给我算。算算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邵康节一听:这叫人话吗?你手里拿什么东西我怎么算呀?你这是以势欺人呀,不给他算!不算?他今天就得砸我的卦摊儿。算,我怎么算呀?邵康节心里着急呀。嘴上可不能带出来。
“大人,这回我要给你算准喽,您还砸不砸我的卦摊儿了呢?”
“这回你要算准我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但不砸你的卦摊儿,我还启奏皇上封你当神机妙算的军师哪!”——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想的是,这回可砸定啦!
“好吧,那您写个字吧!”
“我不写。每回写字你都能算出来。”
“那您说个字也行。”
“我也不说。说字你连死囚犯都能算出来。”
“那我根据什么算呀?”
大人一想:这话有道理。他手里正拿着把扇子,他顺口说:“就以这扇为题吧!”
邵康节一听,扇子。再一看:不错!九门提督右手拿着把扇子,左手褪在袖子里。就是让我给他算算左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呀?扇子。扇字乃是“户”字下面一个羽毛的“羽”字。户下之羽是什么呀?就是房檐底下的雀鸟呀!房檐底下的雀鸟不是鸽子就是燕子,没别的。鸽子个儿大他手里攥不住。嗯!一定是燕子。热景天儿,燕子还没回南边哪!对!是燕子。
“大人手里拿的是……”
“是什么呀?”
“八成是个燕子。”
九门提督一听:啊,燕子在我袖子里他都算出来呀!八成儿他这卦摊我砸不成啦,看来只有认输啦。可是他眼珠子一转,又想个绝招来。
“不错,是个燕子。”他嘴上说手可不伸出来,还在袖口里褪着哪!“燕子倒是个燕子,你给算一下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呀?”
邵康节一听,心说:你这份儿缺呀,我怎么说呀?我说是死的?你一伸手它叽叽叫。我说它活的,你一使劲把它捏死啦。你这叫两头儿占着呀,好嘞!你两头儿占呀,我给你来个小胡同逮猪——两头儿堵。
“大人!您问什么?”
“我是问你我手里这燕子是活的还是死的?”
“大人!您官居一品,身为九门提督,执掌生杀之大权,要它生它则生,你要让它死呀,它是一会儿也活不了哇!”——九门提督一听:“得,满完!”
明末清初,那儿有个测字先生姓邵,叫邵康节[邵康节(1011-1077),北宋哲学家。名雍,字尧夫,谥号康节。范阳人。后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屡授官不赴,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为百源先生。邵康节研究阴阳八卦,参杂道教思想。过去看相测字等迷信职业者,都把邵看作祖师爷。这段相声以邵为明末清初时人,并出现在北京,虽然是附会之说。]大家都说他测的字灵呀!因此他的生意就特别好,别的卦摊一天难得看仁俩的,有的还能两三天不开张。为什么呢?满嘴的江湖话,净骗人,可不康节先生就不一样啦!出口成章,按字义断事。首先大伙听着次不讨厌。至于是个是个个部灵,那可不能那么说。因为他名声大,即便算得不准,大伙儿也都说“差不离”。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儿个人崇拜。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声呢?因为他给皇上测过字。大伙儿想:皇上都找他测字,那还能没本事吗?所以上他那儿测字的犹多,生意就比别的那些卦摊都好。
他给哪个皇上测过字呀?明朝的末代皇帝明思宗——崇侦。啥!这也是个倒霉的皇上。过去有句俗话“倒霉上卦摊”嘛!要不是倒霉,能去测字吗?
崇侦不是住在官里头嘛,他怎么跑到花市大街去了呢:因为闯王李自成、大西王张献忠还有十三家造反啦!闯王的起义军已经快要打到北京城啦!城里可透着有点儿乱。他微服私访,打算悄悄打听打听老百姓对朝廷有什么议论。再说天大打败仗,他在宫里也烦呀!
他一个人,连贴身太监都没带,脱下龙袍换上一身老百姓的衣裳,带了点儿散碎银子,就出了皇城啦,溜溜达达地就来到花市大街啦。见甬路边上围着好多人,崇祯踮起脚跟住里一看,原来是个测字摊。只见一人刚测完了字,对测字先生说:“邵先生,您多受累
了!我回去照您的话去找,准保能找到。”说完这话,付了卦金,转身就走啦。看热闹的也散啦。崇祯心想:原来这位就是邵康节,怪不得这么多人围着看哪!——连住在深宫的皇上都知道邵康节的名字,您想,他的名声有多大?人一散,邵康节的卦摊就亮出来啦。
崇祯一看这个邵康节长得倒像个念书的人儿,六十来岁,花白的胡须。身上穿得也挺干净。面前摆了个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块小石板,半截石笔;一个木头匣子,里面放着很多的字卷儿。要是测字呀,就抓个字卷儿。不抓字卷儿,在石板上写个字也行。不会写字的呀,嘴说个字儿也可以。
崇祯一想:我这皇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啦,不如测个字问问,我这江山还保得住保不住呀?
“先生,请您也给我测个字儿。”
“您拿个字卷儿吧。”
崇祯心想:他那字卷儿不能拿。写那些字卷儿都是他自己选的,哪个字他都编得有词。“我甭抓啦!”
“那您写个字也行。”
崇祯又想:我也别写了。“干脆我说个字吧!”
“那也好。”
“我说什么呢?”崇祯想。正这么个时候,从背后过来两个过路的,一边走一边说:“兄弟!你开玩笑怎么没完没了的,还有没有完啦?”
崇祯一听:有完没有?嗯,我就测个“有”字吧。“先生!我说个‘有’字吧!”
“哪个有呀?”
“就是有无的有。”
“噢!”邵康节拿起石笔,在小石板上写了个“有”字。“您问什么事呀?”
“我是为国担忧呀!我打算问问大明江山还保得住保不住呀?”
邵康节一听,心里打了个顿:面前站着这位是谁呀?一不问婚丧嫁娶,二不问丢财失物,单单问这大明江山保得住保不住呀?一定不是平民百姓。他回头看了看,卦摊周围有没有看热闹的人。他干吗看呀?他看看要是有人他就不敢说啦。怎么啦?因为那年头是“莫谈国事”呀!万一看热闹的人里头掺杂着一两个东西厂锦衣卫的人听去了,那邵康节就麻烦啦!什么是东西厂、锦衣卫呀?就是专门替皇上打听消息的,谁说了对朝廷不满意的话,当场就能给抓走。
邵康节一看,幸好,卦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小声跟崇祯说:“老乡!这个字您问别的什么事都好。”
“怎么呢?”
“‘有’嘛,没米有米,没钱有钱。您问大明江山保得住保不住呀,可不老太好的。”
“你不是说‘有’嘛,没什么都有哇,怎么问到江山这儿就不好了呢?”
“您问的是大明江山呀!这个‘有’字就不能那么解释啦!您看这个‘有’字,上头一横一撇是‘大’字的一半;下头‘月’字是‘明’字的一半。大明江山上下都剩下一半啦,您想那还好得了嘛!”
崇祯一听,心里吓了一跳:解释得有道理呀!可脸上不能带出来。“先生,我刚才说的不是有无的‘有’,是朋友的‘友’。”
邵康节在石板上又写了个“友”字。“这个字您问什么事呀?”
“还是问大明江山呀!”
邵康节说:“您这个‘友’字还不如刚才那个‘有’字哪!”
“怎么回事?”
“您这个字形是‘反’字出头哇,‘反’字出头就念‘友’呀。反叛都出头啦,大明江山可就危险啦!”
崇祯心里又咯噔了一下。马上改口说:“先生!刚才那两个‘有(友)’字我都说错啦,我是要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个‘西’。”
“噢!您说的是申酉戌亥那个‘酉’呀?”
“对啦!”
“还是问大明江山吗?”
“哎!”
“那可就更糟啦!”
“怎么更糟啦?”
“啊!这个‘酉’字还不如刚才那两个哪!不但大明江山保不住,连皇上都得不到善终。”
崇祯一听,脸都白啦!“怎么皇上还不得善终呀?”
“您想嘛:天下数皇上为‘尊’呀!皇上是至尊天子呀!这个“酉’字就是‘尊’字中间那箍节儿(北京土话,一段的意思)。您说这个‘尊’上边没头,下边没腿,这皇上还活得了嘛!连皇上都缺腿少脑袋,这大明江山还保得住吗!”
崇祯一听:这话有理呀!这江山是保不住啦。我连脑袋跟腿都没啦,还活什么劲儿呀?为了保住全尸,连皇宫都没回就上煤山啦——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找一棵歪脖树就吊死啦!
历史上说,崇祯是在李国祯棋盘街坠马后(崇祯手下名将,被闯王在棋盘街刺伤坠马身亡),闯王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才上煤山上的吊嘛——那是史书误
记。那阵崇祯已吊死半个月啦!王承恩才去凑个热闹,想在历史上留个忠君尽义的好名声——沽名钓誉嘛!他找皇上找了十四五天都没找到,后来才在煤山看见崇祯在那棵歪脖树上吊死啦,怕回去不好交差,心想:干脆我也在这儿将就吧!太监王承恩这才在崇祯脚底下吊死的。他们俩上吊前后相差半个月哪!历史上说两人一块儿死的,那是小道儿。我这才是正根儿哪!
闯王迸了北京啦,市面上也平静啦,邵康节上景山遛弯儿去啦。一看,歪脖树上挂着一个。“我认识呀!噢!不就是那天找我测仨(有、友、酉)字的那位嘛!再一看,下边吊着个太监。“噢!这甭问啦,肯定是崇祯皇上呀!哈哈,我说皇上不得善终,怎么样?上吊了吧?我字儿测得灵呀!”从这儿邵康节逢人便说,见人就讲,他给崇祯皇上测过字,灵极啦!这一宣传呀,就有那么些人爱传话,一传十,十传百,邵康节更出名啦!
这话传来传去就传到九门提督耳朵里去啦!这个九门提督是满人呀!闯王手下哪来满人呀?因为李自成进了北京城,骄傲啦!腐化啦!铜棍打死吴兵部,占了陈圆圆,把在山海关的吴三桂可给气坏啦!“冲冠一怒为红颜”嘛!吴三桂这才下沈阳搬清兵,当了汉奸啦!九王爷多尔衮带兵进关,李自成战死湖北九官山啦。江山易鼎,改国号为清啦。我刚才说的那位九门提督换了满人啦。
当时的九门提督权力可不小,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呀!内九门就是:前、哈、齐、东、安、德、西、平、顺,九门提督衙门就设在哈德门里头。内城那八座城门都挂的云牌——“点”,唯独哈德门挂的是钟。九门八点一口钟嘛!因为九门提督衙门设在哈德门那儿哪!他那儿一敲钟,其他的八个城门跟着敲点:“关城喽!”——您说他权力大不大?
这个九门提督不但是满人,还是正黄旗,黄带子,铁帽子王爷呀!街面上传说邵康节字测得灵呀!给崇祯测过字,说皇上不得善终,崇祯真上吊啦!这话可就传到九门提督耳朵里头去啦。怎么那么快呀?九门提督衙门就在哈德门里头,邵康节就在哈德门外头花市大街摆卦摊儿,没多远呀!那传得还不快嘛!
九门提督听到这话儿,说是妖言惑众:世间有这事儿,测个字就能知道生死呀!这都玄啦!我就不信有这样的事。找他去,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事!提督大人换上便服,出了辕门,跨上骏马,后边跟了八个亲兵小队子,保护大人。就出了哈德门啦。到了花市大街,大人一看,嚯,卦摊儿还真不少,哪个卦摊儿是邵康节的呢?问问。当时翻身下马,这会儿来了个过道儿的,九门提督怎么问呀?他一挽袖子,眼睛一瞪,冲着这个过道儿的,“站住!”
把这位吓了一跳。“干吗呀这是?凶神附体啦!……”
“我问问你,邵康节在哪儿算卦?”
这位一想:有你这么问道儿的吗?我该告诉你呀!刚想发作。仔细这么一瞧呀,又吓回去啦!怎么?他看见这位屁股后头还跟着八个弁兵哪!其中一位拉着马。他不敢发作啦,这位小不了,他说:“您问邵康节的卦摊呀,这儿不是嘛!”
说着他手往马路下一指。怎么往下指呀?在明、清那会儿,马路叫甬道,路面比便道高。提督大人顺着他手往便道一瞧,果不然有个卦摊儿。他就奔这卦摊儿来啦!
“你叫邵康节吗?”
“啊!”刚才他问道儿的时候,邵康节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心想:甭问,这位来头不小呀!
“我听人说你测字灵呀?”
“那也不敢这么说,反正八九不离十呀!”
大人一听,嚯!口气不小呀!“你给崇祯测过字呀?”
“啊!”
“你说他不得善终?”
“他煤山上吊啦!”
“那我问问你:我能不能善终?……嗐!我问这干吗呀!你也给我测个字。算对喽我拿一两银子给你。算不准我可砸你的卦摊儿。”
艺高人胆大,邵康节并没心虚:“您拿个字卷儿吧!要不说个字,写个字也行。”
“那我就拿个字吧!”大人一伸手,就在小木匣里拿了个字卷儿。邵康节接过去一看,是个“人”字。
“此字念‘人’。您问什么事呀?”
大人一想:我问什么事呀?我没事儿。我赌气来啦?心里这么想呀,嘴里可没这么说。“我呀?……我是让你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
邵康节一听,心想:有你这么测字的吗?你是什么人,你自己还不知道嘛!你还用得着测字吗?噢,这是考我呀,找我赌气呀!
邵康节抬头把九门提督上下打量了几眼。看这位六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穿得好:宝蓝横罗的大褂,琵琶襟的坎肩;头上戴了顶纱帽头儿,正中一块帽正是碧玺的;一伸手,大拇指儿戴了一个翡翠的扳指儿,水头儿好,是真正的祖母绿呀!再说他说话那派头儿,显着他财大气粗。嗯!甭问,八成是个当官的。“您要问您是什么人呀?您是一位当官的老爷。是位大人。”
“嗯!”他心想: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呢,认识我呀?不能呀!也许是从我的衣着打扮看出来的。既然他看出我是当官的啦,我再问问他我是文官武官?这他就看不出啦。
‘不错!我是个当官的。你再给我算算,我是文官还是武官?”
邵康节一听:这,我怎么知道你是文官武官呀?有这么测字的吗!可是,再仔细一想呀,大人是骑马来的。武官骑马,文官坐轿嘛!大拇手指儿上还戴了个扳指儿,那是拉弓射箭用的东西,噢!八成是武职官:“大人!您要问您是文职官武职官呀?”
“啊!”
“您是武职官。”
大人一听:哎呀!他还真有两下子哪。“对!我是武职官。你再给我算算我是几品官?什么官衔?”
“这?”邵康节心想:这我没法算。武职官多啦:提、镇、副、参、游、都、守、千、把、外委。我知道你是什么职位呀?又一想:算不准都要砸我卦摊儿,要不算还不得给我发(古时刑罚的一种。即充军发配。)了啊!“您是什么官衔呀?……”邵康节说话怎么拉长声呀?他想词儿哪!他一想:这位是穿便服来的呀,要是穿官服来的就好啦!那还用说吗!官服上前后有补子:文禽武兽。大帽上有顶子:红、蓝、白、金。他一看就知道啦!这位穿的是便服,看不出来呀!“您……您……是几品呀?”邵康节一眼看见大人身背后那八个亲兵小队子啦!大人穿的是便服,可他们穿的都是号衣呀!头上打着包头。号褂子外边套着大红坎肩,青布镶边儿。前后心白月亮光儿。有字:后背心是个“勇”字,前心是“南司”。邵康节笑啦!知道啦!南司是提督衙门呀,北司是顺天府——好嘛!大人身上虽然看不出来呀,可他小队子给他戴着记号哪!“回大人的话,您是当朝一品呀!”
“什么官衔?”
“您是九门提督兼五城兵马司——军门大人。”
“啊,神仙呀!我就不信你测字这么灵,三天之内我非砸你的外摊儿不可。”一赌气就要走。
邵康节说:“启禀大人,您还没给卦金哪!”
“啊!差点把我气死,你还要钱哪?”
“军中无戏言嘛!”
九门提督往他摊儿上丢了块银子,约摸有一两多重。带着人就回衙门啦!——合着闹了一肚子气,还花了一两多银子。“花钱买生气”就是那年头儿留下的。
大人回到提督衙门连饭都没吃。晚上气得睡不着觉。干吗呀?他想主意哪!打算想个主意把邵康节的卦摊儿给砸了!“我说三天之内砸他的卦摊儿,我非砸不可。军中无戏言嘛!”
要说在那种社会,甭说身为九门提督,就是一个弁兵,砸个卦摊儿还不容易嘛!就是剐了测字的也没什么了不起,随便加个罪名就办了。可是堂堂九门提督为了表示自己有能耐,不想随便砸摊儿抓人。他还真想试试邵康节,如果真会神机妙算,还想保荐他当军师哪!
大人一宿没合眼,想了一宿想出个主意来。这个主意可损点儿。天一亮就起来啦,要搁着往天还睡哪。今天他憋着砸邵康节的卦摊儿哪!到了书房把伺候他的给喊起来啦,这跟班儿的叫来喜,四十来岁,细高挑儿,有点水蛇腰,外带是个八字脚。这个样子是好的呀!大人往哪儿一坐,他往旁边一站,甭弯腰,那毕恭毕敬的样子就出来啦!
“来喜呀?”
“哎,伺候大人。”
“今儿你也别在家里伺候我啦,你把我的官服换上,带着八个亲兵小队子,上花市大街找邵康节那儿测个字。什么事你都甭问,就问他你是什么人?他只要说你是当官的,回来跟我说,我就赏你五两银子,带人去砸他卦摊儿。”
“哎,是大人。”
老妈子从后面把大人的官服拿出来啦,来喜把官服一换就往外走。
“回来。”
“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到那儿千万别拿他那写的字卷儿呀,那有毛病,你自己写个字吧。”
“回大人的话,小人没念过书呀,不会写字呀!”
“浑蛋!连简单的都不会写吗?你就写个人字儿就行啦,一撇一捺,这还不会嘛!”
“是,是!”
班儿的来喜出了辕门。大人早吩咐下来啦,八个亲兵小队子拉着马在那儿等着哪。来喜骗腿上马,小队后边跟着,来喜心里这个美呀:想不到我这半辈子还当了这么会儿九门提督。到了花市大街甭找啦,小队子昨天来过呀,认识。拉着马就到了卦摊啦,来喜翻身下马。邵康节一看:怎么?九门提督又来啦,砸我卦摊儿来啦。再仔细一看呀:怎么今儿这位九门提督不是昨天那位啦?北京城有几个九门提督呀?不就一个嘛!睡了一宿长个儿啦。又一看:没错!是九门提督,后头那八个亲兵小队子还是昨儿那八个呀!再一看来人身穿袍褂;前后麒麟补子;头上戴着凉帽枣红顶子——从一品,双眼花翎,冲这套官服准是九门提督呀!——多新鲜呀,这套衣服本来就是他的嘛。可是他再仔细一瞧这人呀,砸啦!体不称衣呀,人瘦衣裳肥。穿在身上就像竹竿挑着这套衣服似的:耸肩膀,水蛇腰。脑袋不大,眼睛倒还机灵,望着邵康节滴溜溜转。下巴颏有几根虾米胡子,凉帽往他脑袋一扣,差不多底下就没什么啦!邵康节一下就看出个七八成啦——冒牌儿货!
“邵康节给我测个字。”
邵康节一听:怎么着?认识我呀!“您是写字呀,还是拿字卷儿呢?”
“我自己写吧!”
邵康节把石板石笔递给他啦!来喜拿笔就像拿旱烟袋一样,五个手指头一把抓。好不容易才画了个“人”字,把汗都憋出来啦!您想,他又没念过书,那字写出来能好看嘛?一撇一捺拉得老长,两笔挨得挺紧。这个“人”字就跟他那长像差不多:细高挑儿。“字随人变”嘛!
邵康节把石板接过来一看:“此字念人。您问什么事呀?”
“我没别的事,你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
邵康节一听:今儿这个怎么跟昨儿那个问的一样呀!甭说一定是昨儿那个九门提督派来考我的。我说得不对他好砸我卦摊子呀!他派衙门里谁来啦?是幕府师爷呢还是听差的呀?嗯,不是师爷,师爷能写这样的字吗?再仔细一看,这人往卦摊前一站,手就耷拉下来啦,水蛇腰儿,耸肩膀,俩眼睛净往地下看(比划)。站在老爷身边伺候惯了,那样子就出来啦。对,不是师爷,是跟班儿的。
“要问您是什么人呀?”
“啊!我是什么人呀?”
“说出来您别生气。您是别人坐着你站着,别人吃饭你看着。
你是个站人。甭转文说白话儿,你是个跟班儿的,伺候人的!”
“啊!他真算出来啦!”——哪儿是算出来啦,是看出来啦。
来喜赶紧就走。邵康节说:“你还没给卦礼哪!”
来喜正想发脾气,可是见街上人多,怕丢“大人”的面子,只好乖乖地在身上摸了几个制钱,往桌上一丢,就回衙门啦。
邵康节一看,笑啦:“没错!就冲他给这卦礼就是个跟班儿的——舍不得花钱嘛!”
来喜回到衙门,到了上房。“跟老爷回话,我回来啦。”
“邵康节跟你说你是什么人呀?”
“他说小的是别人坐着我站着,别人吃饭我看着,是个站人。甭转文说白话,我是个跟班儿的。”
老爷一听,把鼻子都气歪啦!“浑蛋,他愣会算出来啦!你叫什么来喜,干脆明儿你改名叫报丧吧!”——这个九门提督算计不过邵康节,对底下人出气啦。
大人越想越气,一转脸见太太进来啦!“太太,您辛苦一趟,上花市找邵康节去测个字,写个人字儿就行啦!别的也甭问,就让他算算你是什么人?”
“哟!老爷我行吗?”
“行,行!太太出马,一个顶俩嘛!”——这叫什么词儿呀?“他要算错了我带人去砸他的摊子。”——他憋准喽要砸邵康节的卦摊啦。
太太说:“既然老爷这么吩咐,我就去一趟吧!”
“别忙!你穿这身儿去不行,那他还看不出来嘛!换换,换换。把老妈子那身儿换上。把首饰,什么镯子、戒指、耳环子都给摘下来。头发也梳梳,梳个苏州髻。”又吩咐丫头:“去,上厨房弄点锅烟子来,给太太脸上抹抹,让他看不出来。”——您说这位太太是招谁惹谁啦,图什么许的呢?“你还别坐轿,坐骡车去。到了哈德门就下车,别让他看见。你记清楚喽!出城门左手第三个卦摊就是。”——好嘛,这位老爷可真用心呀!
这位太太还真听话呀!打扮好喽坐着骡车就奔哈德门来啦。在城门洞就下了车啦,数到第三个卦摊儿一看,没人测字。
“哟!您是邵康节老先生吗?”
“是是。您测字吗?”
“对啦!”
“您拿个字卷儿吧?”
“不价。我写个字吧!”
邵康节把小青石板、石笔递给太太。她就在石板上写了个“人”字。写完了把石板往桌上一放。顺手把半截石笔就搁在石板上啦。说来也凑巧,她那石笔正好搁在“人”字的上半截啦!这样猛一瞧“人”字头上加一横,就成了个“大”字啦!邵康节问:“您问什么事呀?”
“没别的事,您给我算算我是个什么人?”邵康节一听:这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呀,怎么都问是什么人呀?我看呀你们都不是人,吃饱了没事跟我测字的捣什么乱呀!邵康节一看这“人”字头上搁着石笔,嗯,人字头上加一横不是念大字嘛!再仔细一看。嘿!真有这么凑巧的事,刚才来喜写的那个“人”字没擦干净,留下了一点儿。这一点儿不歪不斜正留在“大”字的下边,三下喽这么一凑合呀,这个“人”字就念“太”字啦!“八成是位太太呀!这?不像呀,这份儿穿章打扮,一脸的滋泥,有太太不洗脸的吗?又仔细一想:刚才她写的时候手伸出来可白白净净,胖胖嘟嘟的跟白莲藕似的。要说这个人怎么长的呢?这不是姜子牙的坐骑四不象嘛!嗯,刚才我看她那手腕子上跟手指头上还有印子,那是戴首饰留下的呀!甭问刚摘下去。要是老妈子能戴得起吗?莫不是九门提督故意叫他的太太取掉首饰,打扮成这样考我来啦?要砸我的卦摊儿呀!嗯,错不了。一定是九门提督的太太。
“您要问您是什么人呀?……”
“我是什么人呀?”
“您是位太太。”
哟,我这扮相都唬不住他呀!赶紧给了卦礼回衙门啦。到了上房,还没容老爷问哪,她就说啦:“老爷!邵康节字可测得真灵呀!他说我是太太。”这句话刚说完,气得老爷汗都下来啦——你说这是何苦呢!
老爷一看张妈站在太太旁边哪!“张妈!你赶紧换上太太的衣服,把太太的首饰都戴上。带着另外四个老妈伺候着你,就坐着太太平时坐的那乘八人绿呢大轿,上花市大街找邵康节测字去。就写个人字儿就行啦!人字儿会写吗?这么一撇,这么一捺,瞧清楚了没有?问他你是什么人?他绝算不出来你是老妈子。他看你这打扮,一定说你是太太,还是大官的太太。他只要说你是太太你就回来跟我说,我重重有赏。赏你五两银子,我带着人去砸他卦摊儿。”——他是非砸邵康节的卦摊儿不死心呀!
张妈照着老爷的吩咐把太太衣裳换上啦!戴上首饰。老爷一看:“不行不行!把头梳一下,梳成两把头,脸上再擦上点胭脂粉,头上也得戴首饰,插点花。鞋不行呀!换上花盆底儿。”——老爷用心呀!从头到脚下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检查,亲自指挥。一点破绽都没有啦,才说:“去吧!带点儿零钱给卦礼。”——想得周到呀!
张妈出来,坐上太太的八人绿呢大轿。后边跟着一辆骡车,坐着四个老妈子就上花市来啦!到了邵康节卦摊儿那儿,轿子打杵。四个老妈子赶紧掀轿帘儿把张妈搀下来——嘿,老妈儿搀老妈儿呀!
邵康节一看:来了位太太。还没说话哪,张妈就先开腔啦:(三河县口音)“先生!您老给我测个字吧!我不拿字卷儿,我自个儿写。”
邵康节一听:哟!太太说话怎么这味儿呀?三河县的县知事的夫人来啦!赶紧把石板递过去啦,不是太太刚走一会儿嘛,她刚才写的那个“人”字还没擦哪!按说张妈把太太刚才写的那个擦了再写多好哇!她没擦,她想:这块石板别说再写一个“人”字,就是再写十个也有地方呀!她拿起石笔就写了个“人”字,正好写在太太那个“人”字旁边啦!
邵康节接过石板一看,是个“人”字。“此字念人,您八成是要问您是什么人吧?”
“对啦,先生您太灵啦!俺还没有说话哪您就知道俺要问啥啦!”
邵康节心想:这还用问嘛,这两天来了好几个写“人”字的啦!凡是写“人”字的都问自己是什么人呀,这不明摆着是串通了来 的嘛,成心要砸我的卦摊儿呀!“您要问您是什么人呀?……”
“哎!”
邵康节一想:看她这阵势,穿章打扮,一定是位官太太。还小不了。坐的是绿呢大轿嘛!一二品大员的夫人呀!八成又是提督衙门来的,九门提督的夫人呀!不对!九门提督能要她当夫人吗?什么模样儿呀!不擦胭脂粉还好看点,这一擦上就跟牛屎堆上下层霜似的。您看这满脸褶子,就跟老榆树皮差不离啦!虽然手上戴满了金首饰,可她这手跟刚才那位的手就不一样啦!那位的手跟白莲藕似的。她这手跟黄瓜似的,一手的口子。甭问,粗活儿做多啦!再说也是巧劲儿,她写的“人”字正好写在刚才那位太太那人字儿的旁边啦!她不是太太,是太太身边的人。哪些人是太太身边的人呀?小姐。有这样的小姐吗?不是小姐。丫头?岁数不对啦,四十好几啦。决不能是丫头。嗯,老妈子?对啦!她一定是老妈子。怪不得她说话是三河县的口音呢?三河县出老妈儿嘛!“你是个老妈子呀!”——他又研究出来啦。
张妈一听:得!我那五两银子没啦!给了卦礼转头就走。
四个老妈过来啦!刚要搀张妈上轿,张妈说:“还搀个啥劲呀,人家都算出来啦!坐啥轿呀,咱们自个儿走回去吧。”她这一说呀,连邵康节都给逗笑啦!
张妈回到衙门,跟老爷一回禀呀,把九门提督给气得直咬牙!“邵康节,我不砸你卦摊儿,我这九门提督不当啦!”——干脆说,不砸卦摊儿,死不瞑目啊!
“来人呀!”
“喳!”
“去到监狱提个犯人来。要提判死刑的,判徒刑的不要。”干吗要判死刑的呀?他跟邵康节拼上啦!难邵康节呀!邵康节万万也想不到死刑犯人还可以上街测字呀!
差人在监狱里提了个死刑犯人。九门提督提犯人狱官还敢不给嘛!是个秋决犯。
在前清死刑有两种:一种是斩立决,就是宣判后就给宰啦!另一种叫秋决,就是秋后处决。每年秋分刑部把当年要杀的犯人名单造皇表,皇上还要上天坛祭天,焚了表后集中一块儿杀!前一种是“零卖”,后一种是“批发”;买主都是阎王爷啊。
带来的这个死刑犯叫“该死”,是个江洋大盗。差人把该死带到后院,往那儿一放。
老爷说:“你判的什么刑呀?”
“回大人,小的判的秋决。”
“你想不想活呀?”
“大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还转文哪。
“唔,我给你条活路。给你打扮打扮,你上邵康节那儿去测字,让他算算你是什么人?他要算不出你是死刑犯,回来就放了你。万一他要算对了,那也是你命该如此。”
该死一听:管他呢!碰碰运气吧!“我谢谢大人。”
“来人呀!”
“喳!”
“把他的脚镣手铐给下喽!找剃头的给他刮脸打辫子。洗干净啦给他换身儿干净衣裳,让他上邵康节那儿去测字。我就不信邵康节能算得出来他是死刑犯!判了死刑还能上街测字吗?”——他这招儿可厉害呀!时候不大就把这死刑犯给打扮好啦。
“来呀。派四个人跟着他。”干吗要派四个人跟着呀?一来怕他开溜,二来万一邵康节要算出来他是死刑犯,拉回来不是还得宰嘛!“你们四个离他稍远点,别让邵康节看出来。别穿号衣啦,都换上便服;带着点儿家伙。听见了没有?”
“是!老爷。”
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怕邵康节算出来呀!
四个小队子押着该死上花市来啦!到了邵康节那儿,该死说:“先生!您这字儿测的灵不灵呀?”
“我这儿测字断事如神。”
“啊,灵呀!”
“灵极啦!”
“哎呀!这不要命嘛!”
邵康节一听:怎么?我算得灵怎么会要他的命呀?这个人语无伦次呀。“您是拿字卷儿呀还是写字呀?”
“我说吧!”
“您说个字也行。”
该死一想:我说什么字儿呀?说什么字也不保险,这可是性命交关呀!干脆我就问他我是什么人?只要他一出口错喽,我撒腿就跑。我这官司就算完啦!“先生,字儿我也甭说啦,干脆您就算算我是什么人吧?”
邵康节一听:噢!他也是算这事儿。八成他们是一事吧!这又是提督衙门派来考我,要砸我的卦摊儿呀!“你要问你是什么人呀?……”
“对呀!”
邵康节又一想:我是什么人?人从口出,也就是口字里边加个人字。这字念囚。噢,囚犯呀!有门儿!连囚犯都给我派来啦,你损不损呀!这?不能呀!囚犯能随便上街测字吗?哎,这是九门提督让他来的呀!九门提督支使囚犯,他正管呀。邵康节又上下打量该死,看他一脸的横肉,走路罗圈腿:这是趟镣趟的呀!罪小不了,都趟上镣啦嘛!又一眼见那四个小队子啦。虽然都换了便服,可长相早认识啦。这两天来了三回了嘛!
“你是什么人呀?……”
“是呀!您快说呀!”
“你是个犯人。”
“啊!算出来啦,完啦!我这脑袋要搬家。你缺了德啦!你呀……”
“你不但是个犯人,你这罪还不轻。你呀,活不了!非宰了你不可。”
该死一听:“我可不是活不了嘛,你算灵啦我还活得了哇!”
其实邵康节也没看出他是死刑犯——他怎么看得出来他判的什么刑呀!邵康节说:你活不了,非宰了你不可,是句气话。心里说:你个犯人跟着咋乎什么呀,起哄呀!我还不骂你两句嘛——邵康节那两句本来是骂该死哪,该死认为邵康节算准了自己是死刑犯哪,要不怎么叫该死呢!
四个亲兵过来啦!锁链往该死脖子上一套。“走!押回去。”
邵康节一看:“怎么样?是个囚犯吧!你们那几手儿还瞒得过我吗?”
小队子回去跟九门提督一回禀。把他给气得呀:“来人呀!”
“喳!”
“把该死给我宰喽,甭等秋后啦!”——得!等不得“批发”就给“零卖”啦!
大人还想主意呀,他不认输呀!天儿都黑啦,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吧。气得他一宿没合眼。虽然他一夜没睡可想起个绝招儿来。什么绝招呀?他往日在院子里乘凉呀,看到房檐下有个燕子窝。他打算就在燕子身上出点主意。第二天一早他叫人搬梯子上房给他掏燕子。当差的一听:我们这老爷是什么毛病呀?要玩儿燕子呀!大人吩咐下来啦,不敢不听呀,赶紧搬梯子上房掏燕子。您想人一上梯子那燕子还不飞嘛,大燕子全飞啦!可小燕子飞不动呀,才长毛儿呀,当差的掏了个小燕子下来啦。大人往手里一摸,叫了二十几个亲兵小队子:“你们每人带根檀木棍儿,走!上花市。”他要砸邵康节的卦摊儿啦!他想:就算你邵康节是神仙,这回你也算不出来啦。
他带着人到了花市,邵康节一看:九门提督又来啦!后边还跟着二十几口子,每人手里提拎着根檀木棍儿,甭问是要砸我卦摊儿呀!我得留神点儿。
“邵康节,我又来啦!我甭说干什么你也知道。前天我说:不出三天你只要有一回没算准,我就砸你卦摊儿。咱们说的是三天为限,今儿是第三天啦!这就叫‘军中无戏言’。昨天那些什么太太、老妈子、死囚犯都是我派来的,就是要……我都告诉他啦!——告诉你啦你也得给我算。算算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邵康节一听:这叫人话吗?你手里拿什么东西我怎么算呀?你这是以势欺人呀,不给他算!不算?他今天就得砸我的卦摊儿。算,我怎么算呀?邵康节心里着急呀。嘴上可不能带出来。
“大人,这回我要给你算准喽,您还砸不砸我的卦摊儿了呢?”
“这回你要算准我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但不砸你的卦摊儿,我还启奏皇上封你当神机妙算的军师哪!”——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想的是,这回可砸定啦!
“好吧,那您写个字吧!”
“我不写。每回写字你都能算出来。”
“那您说个字也行。”
“我也不说。说字你连死囚犯都能算出来。”
“那我根据什么算呀?”
大人一想:这话有道理。他手里正拿着把扇子,他顺口说:“就以这扇为题吧!”
邵康节一听,扇子。再一看:不错!九门提督右手拿着把扇子,左手褪在袖子里。就是让我给他算算左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呀?扇子。扇字乃是“户”字下面一个羽毛的“羽”字。户下之羽是什么呀?就是房檐底下的雀鸟呀!房檐底下的雀鸟不是鸽子就是燕子,没别的。鸽子个儿大他手里攥不住。嗯!一定是燕子。热景天儿,燕子还没回南边哪!对!是燕子。
“大人手里拿的是……”
“是什么呀?”
“八成是个燕子。”
九门提督一听:啊,燕子在我袖子里他都算出来呀!八成儿他这卦摊我砸不成啦,看来只有认输啦。可是他眼珠子一转,又想个绝招来。
“不错,是个燕子。”他嘴上说手可不伸出来,还在袖口里褪着哪!“燕子倒是个燕子,你给算一下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呀?”
邵康节一听,心说:你这份儿缺呀,我怎么说呀?我说是死的?你一伸手它叽叽叫。我说它活的,你一使劲把它捏死啦。你这叫两头儿占着呀,好嘞!你两头儿占呀,我给你来个小胡同逮猪——两头儿堵。
“大人!您问什么?”
“我是问你我手里这燕子是活的还是死的?”
“大人!您官居一品,身为九门提督,执掌生杀之大权,要它生它则生,你要让它死呀,它是一会儿也活不了哇!”——九门提督一听:“得,满完!”
6629446466 2025-07-18 16:55